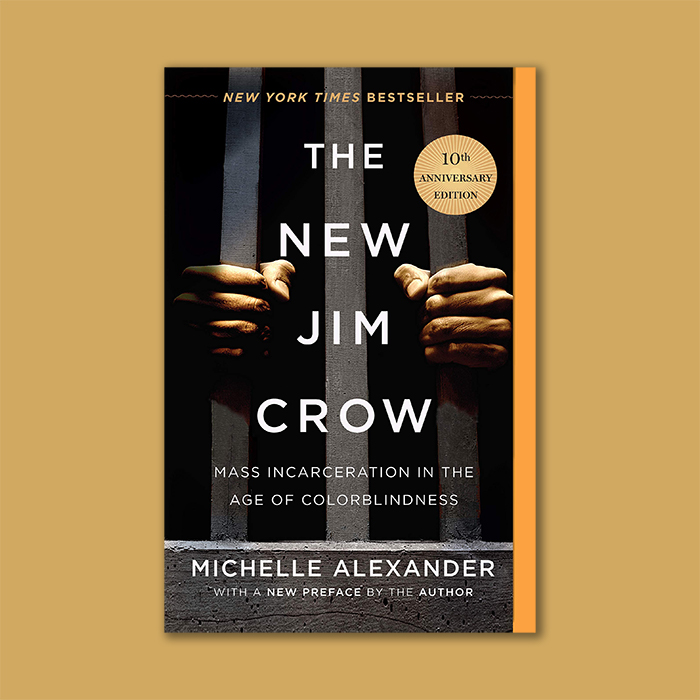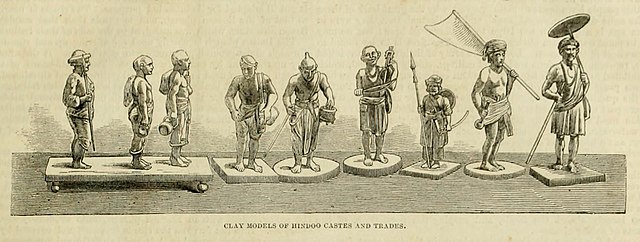深夜,我与同事在桌前等待着一通来自西班牙的电话。这是一场特殊的访谈,尽管我们都有丰富的采访经验,但这次仍有些紧张。因为将与我们连线的,是中国新闻界杰出人物之一——柴静。她的回忆录《看见》激励了一批包括我在内,梦想通过新闻工作带来社会进步的中国青年记者。这是她在过去十年中第一次接受公开采访。
2015年,辞去了CCTV(中国中央电视台)工作的柴静自费制作了纪录片《柴静雾霾调查: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》(以下简称为《穹顶之下》)。该片运用数据揭示华北地区空气污染危害,并曝光了当时环境监管的不健全,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,更有西方媒体称其为中国版“寂静的春天”。2月28日,《穹顶之下》一经发布即获得超过3亿播放量。人民网(中国主流媒体)在同日发表了对柴静的专访。然而仅仅七天后,中宣部下令将《穹顶之下》全网下架。人民网专访也从官网上被删除,柴静随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。
重返舞台
2017年,柴静与家人搬到了西班牙巴塞罗那。临行前,她把工作时穿过的西装都送了人,这是一个卸甲归田的动作。
她说:“我下定决心,只是生活,不再工作。直到一个月后,我与家人经历了一场恐怖袭击”。在这场暴动中,三岁的男孩哈维丧生街头。
作为一名中国记者,恐怖袭击对她而言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概念。但她决定重返新闻现场。这个决定来自哈维的父亲,他恳求人们去寻找真相。柴静说:“我是一个欧洲的陌生人,对它的语言、文化、宗教几乎一无所知。但是我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”。
2023年8月17日,在公众视野消失了将近十年后,柴静携她的新纪录片系列《陌生人:对话圣战分子》(以下简称为《陌生人》)在YouTube回归。这部纪录片通过与前伊斯兰极端分子对话,剖析暴力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和动机,短时间内吸引了超过20万次观看。柴静曾试图在中国网络平台发布该系列视频,但视频在发布后一个小时内被删除。
柴静在制作期间没有去想《陌生人》最终会以怎样的形式与观众见面,对未来限制的考虑会成为思考探索的障碍,这是她不愿意接受的。她认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,该选题都具有敏感性和宣传的禁忌性,如果过早地去考量发布的困难,《陌生人》就不会是如今这样的形态。
作为一个欧洲的“陌生人”,柴静无疑面临着一个有难度的选题——她没有在中国那样广泛的人脉,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。但困难会提纯一个调查者的动机。她说:“假如这件事情是我真正的疑惑,我又有足够的真诚去把它探索到底的话,(那么)我有一天有可能能够走到桥的那一端去。没有这个信念,我觉得是不可能走下来的”。
新舞台
柴静在她的 YouTube个人频道继续着探索的脚步。尽管运营个人账号对她来说是一个全新体验,但适应媒介转变的心路历程却并不陌生。
她说:“我们身边的环境一直在变化,媒体的环境也一直在变化。可能每一个阶段身处其中的人都认为自己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但对我来讲,如果你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想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…你(就要)像水一样流淌,你(无论)遇到什么样的环境,你会变化自己的形态,与环境发生碰撞,有时候是搏击,有时候是顺流而下的一种顺畅。环境在变化,但是流淌的这个动作其实一直在”。
“(虽然)媒体的形态一直在变化,但实际上你做传播的愿望是没有改变的。自媒体的出现,实际上是把中间的技术障碍、平台障碍、运营障碍取消了,所以你有一个在这个平台 上直接跟你的读者、观众面对面交流(的机会),(并)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来生产节目, 而且没有审查环节,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挺欣喜的事情”。
自2010年以来,柴静就在博客上与她的观众保持着互动。博客,在中国早期互联网最兴盛的交流形式之一,逐渐在网络媒体迭代中没落。X(前身为Twitter)为她提供了更多自由的筹码。过去一年中,柴静都活跃在X,她在上面与观众交流,有时候也更一些日常的帖子。“看见”是她2012年出版的畅销书的书名(该书于2023年被翻译成英文),但“倾听”仿佛是她另一个使命。
柴静有时会在X上面分享读者的来信。她在2024年1月10日的帖子中写道:“谢谢大家的信…今天有位读者为笔下的“负面”情绪道歉。不用。我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‘负面’或者‘正面’的,只觉得大家写得很真实,这真实感充实了我,这正是我当年进入这个工作的原因。像当年电台节目一样,我很少给别人建议,只回信问几个问题。另外,陌生人彼此的回信,比我能说的更深广”。人们写各种各样的信给她,内容有时是对她的调查的讨论和提出问题,有时候是他们的个人成长故事。大多数信件作者都要求匿名或使用假名。
当谈到与观众互动给她带来的影响,柴静说:“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的直接。比如说我会从里面找到一些新闻线索什么的。这个我不排除,但是我不想那么功利。我跟读者和观众的关系,我希望是一种礼物”。自发性对于这样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:“我没有功利的目的,比如说他们在推特(X)上给我写信,对方不是为了让我采访他或怎样,它是一种表述,就是我在那时那刻,我想给你写一封信说一说,而且我知道你愿意听”。
新闻的本质
尽管内容的产生方式和与观众们的互动形式改变了,新闻的本质却亘古未变。柴静始终相信媒体的责任是揭示。
“有些问题在你准确地揭示它的同时,好像它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答”,她说。法里德·本耶图,一位前圣战分子,在《陌生人》中接受了柴静的采访。他曾告诉她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问题说清楚。” 这样的认知也体现在柴静的朱令案系列访谈节目中。这三期访谈节目回顾了发生于1994至1995年,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被多次投毒,而嫌疑人仍未被绳之以法的悬案。柴静分别访谈了对朱令头发进行了检测的科学家贺敏、朱令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童宇峰,和朱令的父母。柴静说,“破案不是我的职责,我要追诉的事是:是什么导致了一个案件没有侦破…是什么因素,这个因素是正常的吗?”
事实核查对柴静来说是另外一个关键。“在这个平台很多人把自媒体的‘自’理解为个人表达…但对我来说,它还是一个报道”,她强调道。
朱令案是柴静完全通过互联网做调查性新闻的全新尝试。事件发生在1994年的中国,因此涉事人、舆论反应等也都存在在中国。而调查此案时柴静身处与事发将近30年后的巴塞罗那,要溯源该案,就要跨越地理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鸿沟。互联网为她提供了更多追溯的条件。朱令案中的一切采访、报告、物证均是柴静通过线上整理。但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,如何核查和使用这些信息就变得关键。
“如果你注意的话,你会看到我使用的这些通信和贴文,第一我对他们都有比较严格的依据上的要求。比如说我使用了她(朱令)的室友王琪和朱令母亲的通讯记录。这个记录对 我来讲算是一手的信息。记录的时间点,她们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谈的…当时有没有 发给第三方作为一个旁证,这些我都经过核查,我跟第三者也都经过验证”,柴静说。
对柴静来说,比起政治和商业上的压力,她最大的焦虑是:当面对观众的时候,她对自己所说的话心里没数。
“做媒体,如果你有聪明劲儿,有些事就绕过去了,你不提,别人也不提,说不定就过去了。可是你自己心里知道得一清二楚:那个事儿你没弄明白”。
柴静因此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“笨功夫”。在朱令案中,为了找到朱令被投毒的渠道,她建立了由四位研究与生物学相关的博士组成的志愿者小组。“(我们假设了)如果是在咖啡里投毒的话,那么有没有可能铊盐的颗粒由于密度、大小与咖啡颗粒不同,透过速溶咖啡的颗粒向下沉积,从而导致底部浓度更高。为此我们还用计算机模拟了一下颗粒沉降的速度。这些是不会用到的,我自己很清楚,但是我想让我自己心里有数”,她说。
从心所欲,不逾矩
网络平台或许为柴静带来了创作自由,但这不代表她不受任何约束。“我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来做成绩,可是我要考量的因素太多了,我要考量身在国内的人”,她说。
在朱令案中,柴静展示了一段朱令母亲与警察交谈的录音。“我甚至要考量说出那段录音 的那位警察的处境…如果我不考虑这些,如果我考虑的是要我的节目有更多的影响力,那可能会是完全另外一种做法。但是我要考虑人,考虑现实,远在一万公里之外的故土的现实。”
“他们不知道媒体的后果。即使你在采访的时候,你询问了他,他说没有问题。从新闻伦理上来讲,你好像觉得可以了:我已经告知对方,对方已经是成年人(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),可是别人真的不知道媒体播出之后的后果是什么”。
董宇峰,朱令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,在节目中接受了柴静的采访。他的照片因此曾出现在那一期节目的视频封面。但节目播出后,他的家庭陷入了恐慌,因为他们时不时会接到关注这件事的观众的询问电话。柴静因此将封面上他的照片换成了清华大学大门的图片。
柴静的保护不仅限于她的受访人。在整个访谈过程中,柴静的声音都坚定而沉稳,唯有提到志愿者的时候,她频频叹气。
“我播出一个节目之后,是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的,可跟我合作的人能得到什么呢?他们没有署名,”她说,带着一些惋惜。“不是我不能给他们署名,也不是他们不想署名,可是他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。”这样的代价是什么,柴静没有说。
尽管她十分珍惜且感激志愿者提供的帮助,但良心上的负担使她无法再继续与他们合作下去。“我做YouTube的时候决定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,我要一个人工作”,她说。“这是一个美好的悲剧”,她补充道。
脱不下的战袍
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巴塞罗那的凌晨,但柴静的声音丝毫不显疲惫。事实上,她的每一期节目几乎都在这个时间段播出,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作息。曾经抱着隐退的心情远走他乡,如今她的工作却又在新的平台落地生根,她为此乐此不疲。
“你琢磨这件事的那一会儿,你从早上坐到桌前头,一眨眼天黑了,再一眨眼天亮了。头上日升月落腾云翻滚,你能想象那个感觉吗?这就是过日子,相当美好,我不知道这世界还有什么其他事情比这更好,所以我就聊以度日,这么干下去”。
对于未来要出版的书和正在筹划阶段的播客,柴静没有做详细的规划,但重新穿上的战袍恐怕是很难再脱下了。